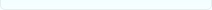- ±Ψ÷ήΥΌΉx≈≈––Αώ [Ή÷/Ζ÷γä]
| 1 | * | 3200 | |
| 2 | ½ν* | Κΰ±±ϋS¨υ | 3000 |
| 3 | * | 2500 | |
| 4 | * | 2300 | |
| 5 | * | 1500 | |
| 6 | * | 1000 | |
| 7 | * | 900 | |
| 8 | * | 700 | |
| 9 | * | 600 | |
| 10 | * | 600 | |
| 11 | * | 500 | |
| 12 | * | 500 | |
| 13 | * | 500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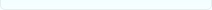
| 1 | * | 3200 | |
| 2 | ½ν* | Κΰ±±ϋS¨υ | 3000 |
| 3 | * | 2500 | |
| 4 | * | 2300 | |
| 5 | * | 1500 | |
| 6 | * | 1000 | |
| 7 | * | 900 | |
| 8 | * | 700 | |
| 9 | * | 600 | |
| 10 | * | 600 | |
| 11 | * | 500 | |
| 12 | * | 500 | |
| 13 | * | 500 |